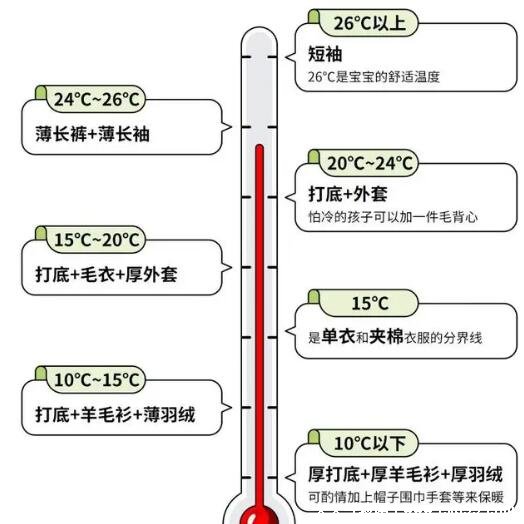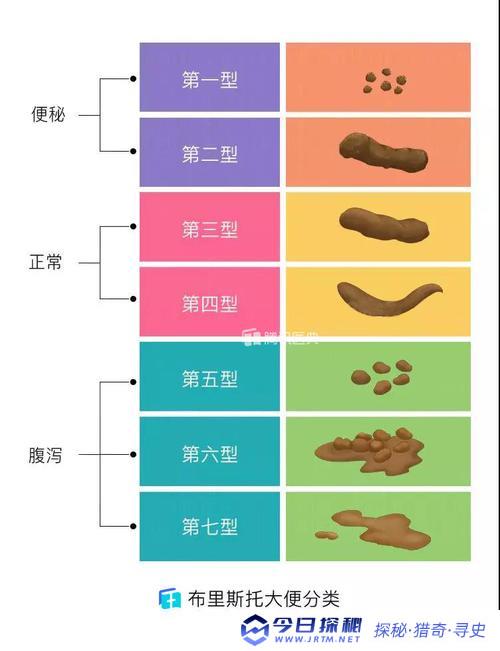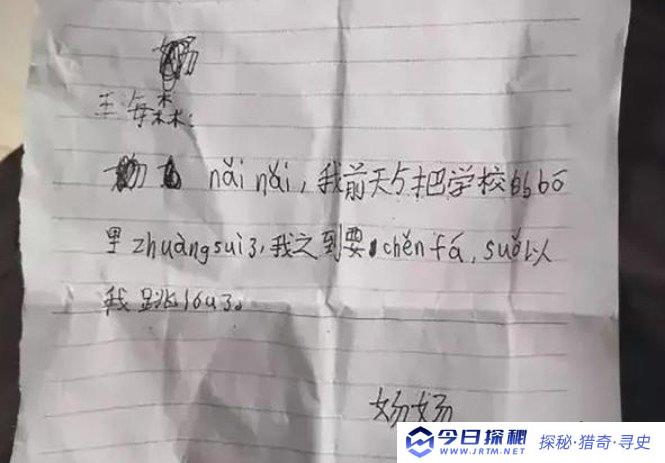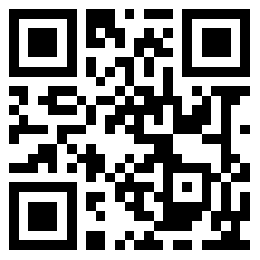本文作者谢正光(图右)与岛田虔次。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3日《南方周末》)
1966年3月,我在新亚研究所攻读硕士的第二年,获日本文部省颁发奖学金前往京都大学进修,为期两载。申请表上填写的系别为“东洋史”,研究方向为“宋代文人生活”。
同年4月抵京大报到,始知宋史专家佐伯富(1910-2006)教授专治经济史,著有《宋代茶法研究资料》与《清代盐政研究》,日本学生中多称之为“茶先生”及“盐先生”而不名。教授又擅于编撰索引,举凡《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苏东坡全集》《宋史职官志》《中国随笔杂著》《六部成语》,乃至清人黄六鸿之《福惠全书》等书,均在网罗之列。
由于治学方向与教授不相合,遂与东洋史研究室渐行渐远,转而投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岛田虔次(1917-2000)先生门下。
岛田先生,广岛县人。1941年以研究阳明学之论文毕业于京大史学科,时任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授。多年后,我在耶鲁当研究生时,读到一位美籍汉学名家讨论晚明思想家李贽的文章,其观点与取材皆来自岛田先生1940年代的作品。
及1968年3月,文部省奖学金结束, 居留权亦到期,我前往大阪“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刚表明来意,值日管理官员即出示一信件,署名“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田村实造教授”。信中指出我到京大东洋史研究室后, 从未参加任何学术活动。建议延期居留之申请,严词拒绝。
此岛田先生有第一信之来由也。
第一信:岛田虔次先生致大阪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函
拜启:
今日猥蒙来电,询问本研究所研修员谢正光君之事,惶恐之至。余对于谢君看法,一如电话所禀,惟尚有一事忘记奉告,即关于其“研修员”身份,谨此附笔:
今年三月以前,谢君一直在京都大学文学部担任研修员一职。所谓“研修员”者,与学生有别。学生须到堂上课,接受考试并获取学分,而研修员则没有以上这些要求(相应地,也没有获得学士、硕士之类学位称号的权利)。大体研修员者,乃是针对教授会认可的具备学者资格之人,为了给予其在学部或研究所进行研究的便利(特别是可以自由利用图书或仪器,并参加研究会)而设的制度。因此,即便在学部的场合,称为研修员者〔其程度〕亦大致在大学院毕业生以上,不然的话,也是作为听讲生(这是要通过选拔考试录取的),其间有明确的区别。【眉注:当然,有时候为了取得学位资格,也有从研修员起步参加考试进入大学院的人,但这是例外的情形。】就以本研究所的实情为例,目前有来自欧美的研修员数人,皆为彼处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或至少是大学院的毕业生(其中许多是为了完成将要提交给母校的博士论文而来到日本)。职此之故,余等虽经常担任研修员的指导教师,但也有就在最初办手续的时候见过一面,从此以后便几乎见不到本人的情况(因为他们要么是忙于学日语,或者,除了时而来看看书,就在家里或图书馆里做研究了。对方学者当中,这样的人也很多。)总之,正是因为存在这些状况,把研修员不来上课这件事小题大做,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合道理的。那一边是否有什么误解呢?还是因为相对于研究所而言,学部教师主要跟学生打交道,不知不觉中就有把[学部的]研修员与学生同视之的倾向(特别是在谢君这样年轻的情况下)?在我眼中,谢君毋宁说是一位相当勤勉的研究家。(虽然他或许没有来听文学部的课程,却总是在本研究所的图书室学习。)其论文的眼光也非常出色。我想,只要一读他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便可知其为实力充沛且大有希望的学者。思想上也完全没有过激的地方。余与谢君谈话之际,常受其学问上启发,心存感激。虽名为指导教师,实际上不如说是当作友人在交往。(其人品亦温厚,属于谁都会喜欢的类型。)因此,今天接到贵处来电,殊觉讶异。(因为从一开始就是本研究所的研修员的话,照理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故不揣冒昧,呈此一函,欲为之开释误解。或者殊为多事之举,敬祈海涵,并申问候。不宣。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授
岛田虔次
四月十五日
此呈
出入国管理事务所 钧座
【附注:来电人员的名字不小心忘记了,谨申歉意。】
信中所谓“学部教官”,即田村实造(1904-1999)教授。蒙元史专家,所撰《中国征服王朝の硏究》(1964),著名于时。夷考其实,1945年东京东亚研究所(日本军阀侵华理论之大本营)刊印《异民族支那统治史》,考论自北魏至清朝之统治政策,田村教授啼声初试。严格来说,他其实是异民族支那统治史的专家。
田村教授比岛田先生长13岁。田村于1947年升教授后,即兼任文学部部长。就年龄、职位而言,田村皆先生的“先辈”。信中称“学部教官”,盖由此故。
凭先生一封信,我得在京都游学三载。得奉手者,还有名满天下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教授。教授乃业师牟润孙先生北平旧识。余以“曾国藩幕府人物”请教。吉川教授建议可采史汉纪传体,处理曾幕人物。
近日得读先生高弟狭间直树《“中国近世主观唯心论”的思想史建构——岛田虔次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一文,述岛田、吉川两先生的关系说:
岛田先生隶属于经学文学研究室,受到主任吉川幸次郎的诸多熏陶,1946年3月经吉川先生夫妇的媒妁而与藤井元子女士结婚。(《汉学研究通讯》22:1,2003)
京都两位曾有恩于我的异国友人,彼此间还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这是当年不知道的。
岛田虔次青年时代的读书批注
第二信:致耶鲁大学历史系芮玛丽教授
谨覆:
拜诵11月14日来翰,关于谢正光(Andrew C. K. Hsieh)其人的询问,谨答复如下:
谢氏1941年生人,今年当已廿七岁。其家世居广西容县,想来大概是地主。谢氏生于斯长于斯,1951年十岁之际与双亲及弟、妹一同移居香港。小、中、大学教育皆在彼处完成。大学就读新亚书院(中文大学),继而攻读该校研究所研究生。1966年4月,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来日,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学习日语半年后,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大学院研修员的身份,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今年4月转为本研究所研修员,研究题目为“曾国藩及其幕宾”。此外,其家庭情况是:其父系沙捞越一所华人中学的中文及中国历史教师,母亲及弟、妹各一人(高中生)均在香港,听闻另有弟、妹各一人在大陆。其母在家为主妇。
谢氏来日以后发表的两篇论文《宣南诗社考》《同治年间之金陵书局》(均载《大陆杂志》),想必已蒙浏览。故关于其学术上的能力,或许无须赘言。但就平日接触见闻言之:其研究态度之热切固不待言,汉文读解能力之强,眼光之敏锐,更是余所确信。上述二论文虽取较小题目,然史料之博搜,论断之明快,对这一年龄的研究者而言,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特别是他研究幕宾的方法,乃是在彻底调查大量幕宾传记的方针下,只要是能看到的史料——地方志固不待言,相关人物的文集、随笔之类亦无不专心涉猎、竭泽而渔。这种做法固然理所应当,却不能不说是令人佩服的。究极言之,此乃中国旧派学者擅长的路数,但我们可以看到,谢君在这些方面也有着突出的能力。
此外,谢君还经常参与我们的“辛亥革命研究班”(班长是小野川秀美教授),积极发表意见,诚可感谢。
他的日语未必能说是十全十美了,但会话是没有问题的,跟我谈话全操日语。无论是非常复杂的情形,还是高度学术性的话题,他都可以用日语充分地表达,发音更是无可挑剔。
上面所说,虽然未免让人觉得净是些夸奖,但决不是刻意做作的说辞。此皆余作为指导教师率直的见地。要之,可以这么说,谢君乃是我历来接触中国留学生当中最为优秀的一位。尽管我并不清楚地知道他立志赴美的终极目的,但细察之下,大概是有志于获得美国大学的教职吧。正如您所了解的,中国学者要想在日本找到合适教职可是相当困难的,却又不甘心困在香港那般狭小的天地——我推测,这便是他的想法吧。
就余所见,谢君当前的研究状况略如上述,要多说一句的是,谢君在学问上的素养和关切决不限于近代史。他在香港的毕业论文是有关春秋时代的题目,还发表过关于《廿二史札记》作者问题的考证。日常与余谈话之际,也能清楚地窥见他对于中国学术的素养,尤其是其知识大要正确,是余特别抱有敬意的地方。
至于他的性格,可以说是快乐而积极向上,人际交往也相当顺畅,并且完全没有那些政治色彩(无论对右派还是左派)。稍有些遗憾的是,由于文部省奖学金按规定在今年3月以后就停发了,谢君不得不自己挣学费。目前一边在京都的YBU英语中心(美国系天主教会经营)担任英文教员,一边继续做研究。然而,尽管做着非常费时的工作,却还是每天在研究所的阅览室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如此拼命地学习,实在让人感动。我衷心祈盼他的志愿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
以上内容是针对来信中所说“ability, potential and ultimate career motivation, approximate age, family status, the part of China from which the family came, what kind of man, coming from what kind of background, aiming toward what kind of goal”等问题来回答的。我的英语不够好,或许对您的问题有把握不准确的地方。若有不尽之处,敬请随时赐示,定当尽我所知给出答复。
敬祈自珍为先,并请转达我对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教授的问候!
岛田虔次
11月24日
此致
芮玛丽(Mary Wright)教授
芮玛丽(Mary Wright)教授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教授,均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之门生。二人于太平洋战争前在北京访学,及珍珠港事变,同被下狱。1945年被释后,留华搜购近代文献,即今日斯坦福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所藏之奠基物。1959年,贤伉俪移席耶鲁大学,芮夫人(Mrs. Wright)先后完成《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tion》(中译本名为《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及《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7》(《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
我于1969年5月中到耶鲁报到,旋注册入暑期班进修“法文阅读”。同年秋,修读芮夫人之近代中国研讨会。与会者共十人,每周由两位同学就指定阅读文献分别提交短文一篇,由第三位同学主持讨论。芮夫人端坐,或点头微笑,或指斥所论之谬。如是者十二周始结束。
大概是1970年1月中,我在总图书馆偶遇芮夫人。彼此皆行色匆匆,只记得临别时芮夫人对我说了一句话:“谢先生,再见啦!”
同年6月18日,芮夫人与世长辞。得年52岁。下葬于耶鲁墓园。
和耶鲁结缘,岛田先生自是重要的牵线者。从逰于两位芮教授门下前后七年,悲喜交集。他日有缘,当另作一文叙其始末。
岛田先生信中所及“曾国藩及其幕宾”一项目,限于种种规定,终无法完成,其后草草以《儒将曾国藩》一文取得毕业。正如在新亚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春秋城筑考》,我的“制艺”文字,早已蛛网尘封多年。
《中国思想史研究》书影
傅佛果译介的《岛田虔次:学者、思想家、读者》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书影
第三信:致谢正光君
1996年岁暮,绛云和我带同小儿君山,从美西直飞东京。离家前,给岛田报告行程。及抵东京,收到先生一封急递:
敬覆:
前日拜收赐信,以及大著《明遗民传汇刊》诸种,学兄不断向学界作出贡献,真心敬服之至。其后起居无恙,是所至祷。余去岁虽苦于剧烈腰痛,今年幸无再发,得以健康度日。眼下工作,则集中全力与“人文研”诸人共同译注《梁启超年谱长篇[编]》。近况如此,敬请放心。(小生于1981年达到年龄退休,现为名誉教授。)
本月末尊驾来日,一月初将莅京都,相隔十六年,得再度面晤畅谈,至为企盼。此次尊夫人、世兄也相伴同来,同样期待与他们的初次会面。目前来看,一月初我这里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惟慎重起见,仍盼您能从东京来一通电话。(根据您日程的安排,来京都后打也可以。)我可以在电话里详细奉告来舍下的路线以及交通工具等信息。鄙处电话是:0774-32-xxxx。
专此奉达,敬祈自珍,尊夫人处并致问候。
12月11日
岛田虔次
此致
谢正光学兄
今日重读此信,愧憾犹存。犹忆1969年离开京都,西来就学,完成学位,中经六载。旋即穿州过郡,教书糊口,于1980年得暑假研究津贴,始得于离京都后首次拜见先生。时先生已改任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教研两忙,也就匆匆一面,未得多谈。
及至教职位稳定,绛云来归,君山诞生。公私两忙,转眼十六年,才又得拜访先生,也是和先生最后的一面了!
先生寓庐在京都市近郊宇治。1996年往访,时值黄昏时刻,下车后,幸见灯火通明;打听之下, 先生寓庐,无人不知。
宇治所产抹茶及建成于1215年的神社殿堂,名满三岛。惟直到离开京都六十载后,才发现宇治酿成的“黄樱酒”清纯可口。寒舍近年贮仓的清酒,“黄樱酒”外,便不作他想了!
和先生交往期间,累蒙先生赐我他的著作,且皆有题签,早期的有《龚自珍“尊孔”》(1967)、《辛亥革命の思想》(1968)、《六经皆史》(1970)。最后相见时又赠《朱子学と阳明学》和《三十三年の梦》(1996)。为学术主流而撰者外,还有专为一般读者而写的;这是先生治学特别值得敬重之处。
(岛田先生第一封信,用日文撰写。今承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教授译成中文,谨此致万分谢意)。
谢正光
,